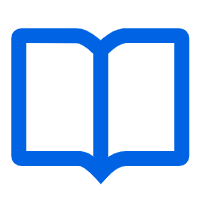为什么欧洲环境好?
我以一个普通欧洲人的视角,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环境”,这涉及到一个定义的问题。我认为的“环境”是指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人文景观(包括城市与乡村),另一类叫做自然景观。而所谓“好”或者“坏”就是指我们对这些自然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些影响有的可以量化,称为“污染”(pollution);不能量化的,如人口密度等,则称为压力(stress)。
由于历史原因,欧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人口的绝对数量不大。在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之后,生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人们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主要是受高等教育之后的高收入和二孩政策的影响。但即使这样,人口的自然增长仍然非常低。据欧盟统计,2016年平均每出生率只有9.8/1000,平均死亡率达到13.5/1000,造成每年近4万人的负增长。[1]可见,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我国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人口总数虽然多,但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却是很大的。下图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注】数据来源:Eurostat 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人均GDP的增长,以及社会福利的改善,欧洲各国的人均碳排放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最高点下降到今天的约一半,每立方米碳排放量约2吨,仅为中国碳排放量的七分之一左右。
在谈到气候变化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早就过了排放高峰,正在致力于减排,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很强。其实,只要看看欧洲各国经过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却依然能不断减少碳排放就知道,气候变化并不是什么不可抵挡的灾难,只要改变生活方式,采取低碳节能的做法,即使是经济危机也能倒逼低碳经济发展。
当然,在讨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时,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找到背后的深层根源。对于欧洲来说,其环保政策和做法有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并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益、社会成本甚至政治意愿来解释。
在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极大地撼动了凯恩斯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政策。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统治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市场被神话,政府被贬损,各国纷纷放宽对产业的管制,指望通过市场的神奇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招并没有使欧美的经济走向腾飞,反而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陷入了“后工业化”的迷茫期。新自由主义的迷弟特朗普就曾经讽刺地称,美国的经济实力被中国的“偷窃”了,原因是他们在制造业上花了太多钱,而我们把这笔钱都花在了军工上。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什么加强环境规制会阻碍经济发展的理论在当下似乎行不通呢?
答案就在环境和生态破坏的身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美各国大量出现了反文化运动(Beat generation)、性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越战抗议活动,环境正义的呼声不断冲击着旧的有罪无罪、好人坏事的思维定式。正如我们在六十年前抛弃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一样,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市场和政府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神迹。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业文明确实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毁灭。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调整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大力加强对于环境的规制,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而且提高了社会运行的费用,包括税收和保险。面对这种困境,一些经济学家又开始呼吁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主张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实现增长与环保的双赢。只不过凯恩斯这回恐怕要看不起眼那些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了。